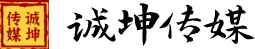林瞪是中国摩尼教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位关键人物,但长期未受到应有的关注。2008年10月以来,在北宋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公(1003~1059年)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的主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专家学者金泽、黄夏年、郑筱筠、陈进国等先生亲临福建霞浦进行学术考察,在霞浦县有关部门等的帮助支持下,并积极发动宗亲和乡贤查找相关线索和各类资料,先后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与文物,数量相当丰富,“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继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发现以来,中国境内摩尼教文献的第二次大发现”。[1] 厥功至伟。这批文物与文献不少都与林瞪密切相关,本文拟以这些新发现的文物、文献为依据,对林瞪其人其事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略作探讨,冀以推动霞浦摩尼教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林瞪与龙首寺
林瞪其人,正史无载,但在福建地方志资料、族谱、家谱及民间传说中却多有叙述,其中以柏洋乡民国壬申年(1932年)纂修的《民国孙氏宗谱》(又作《富春孙氏族谱》)所收《孙绵大师来历》最为有参考价值,兹移录全文如下:
公,孙姓,讳绵,字春山,禅洋人,初礼四都本都渔洋龙溪西爽大师门徒诚庵陈公座下,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966年)肇韧本堂,买置基址而始兴焉,诚为本堂一代开山之师祖也。本堂初名龙首寺,元时改乐山堂,在上万,今俗名盖竹堂。门徒一人号立正,即林廿五公,幼名林瞪,上万桃源境人,真宗咸平癸卯(1003年)二月十三日诞生,天圣丁卯年(1027年)拜孙绵大师为师。[廿]五公卒[于]嘉祐己亥(1059年)三月初三日,寿五十七,墓在上万芹前坑。孙绵大师墓葬禅东墘对面路后。显扬师徒,俱得习传道教,修行皆正果。
文中的孙绵为福建霞浦县西北部柏洋乡禅洋村人,[2] 于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966年)开始在禅洋村东一公里开外的上万村着手营建龙首寺。该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摩尼教寺院,比著名的晋江草庵要早数百年。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建北部太姥山之“摩尼宫”即为摩尼教寺院,以此证明在会昌灭法前福建即有摩尼寺之建。[3] 实则非也。如所周知,在会昌灭法前唐境内所有摩尼寺均为回鹘所建,共有7座,分别位于长安、洛阳、太原及荆(今湖北江陵县)、扬(今江苏扬州市)越(今浙江绍兴市)、洪(今江西南昌市)四州,前三者为唐朝政治中心,后四者皆为粟特商胡最活跃的地区。回鹘摩尼寺的建立,当与粟特的政治经济利益密不可分。[4] 根本不可能建于荒僻的太姥山上。再说,以上七寺均名大云光明寺,不闻“摩尼宫”之谓。质言之,此“摩尼宫”应系“摩尼宫殿”之简称,为佛教术语。明代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主持永觉元贤曾游摩尼宫,并留有诗作:“孤塔迥云际,下有摩尼宫,路古苔长密,庭幽翠欲笼。松枝挂海日,竹影弄江风,汲得岩前水,烹茶论苦空。”[5] 整个诗中禅味十足,完全无法与摩尼教相联系,故其所游之地当为一处佛寺,诗中的“摩尼宫”当为佛寺的代称。这些说明,太姥山摩尼宫为摩尼寺之说完全无法成立。
林瞪及妻女相继皈依之龙首寺,于元初改名曰乐山堂。龙首、乐山,乃回鹘语rošn(借自中古波斯语rōšan)之音译,意为“光明”,恰合摩尼教崇尚光明的旨趣。[6] 该寺开创者孙绵之师为西爽大师之徒陈诚庵。有一种意见认为:“按西爽大师应该是胡天尊、胡古月、高佛日等中的一位,应该就是高佛日……唐以降入闽的摩尼教团,除了有从福州南下泉州的一位传教师——‘呼禄法师’外,还有至闽东宁德地区霞浦、福鼎太姥山一带的一群传教师——如胡天尊、胡古月、高佛日、西爽大师等。”[7] 此说漏洞颇多。案,胡天尊、胡古月、高佛日之谓见于《乐山堂神记》第16行,明言胡天尊、胡古月、高佛日为“灵源传教历代宗祖”。此“灵源”,此前笔者曾误解为摩尼教来源地之意,故释为波斯。[8] 近期读书始知应为今福建泉州市晋江西南之灵源山。明人何乔远著《闽书》卷7《方域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9]
说明灵源与草庵所在的华表山是连为一体的。灵源山、华表山之名,至今沿用不辍。《读史方舆纪要》卷99泉州晋江县条载:“紫帽山……又南十里曰灵源山,蜿蜒数十里,高出东南诸峰。上有灵泉,大旱不竭。一名太平山,以山顶平正也。亦名吴山。”[10] 可证胡天尊等为晋江高僧。会昌以后,将摩尼教传入泉州的为呼禄法师,此人最终卒于泉州并葬于清源山下,故第一代始祖胡天尊应指“呼禄”其人。笔者考证,呼禄为回鹘摩尼僧,为回鹘语Qutluγ的音译,意为“吉祥”,古代汉语文献又译作“骨咄禄”、“骨禄”、“骨都”、“胡禄”等。又考虑到呼禄为回鹘人,故被称作胡天尊。至于胡古月其人,颇有可疑之处。《明门初传请本师》有言:“灵源传教历代宗师胡天尊祖师、高佛日祖师。”内容显然与《乐山堂神记》所载“灵源传教历代宗祖:胡天尊祖师、胡古月祖师、高佛日祖师”相对应,唯其中不见胡古月其人。二者必有一误。考虑到古、月相合恰为“胡”字,故疑“古月”二字甚或其前的“胡”字均为书手笔误,苟以衍误处理。作为胡天尊的第一代传人,高佛日应为胡人(当然不能排除他为灵源当地汉人的可能性)。
将摩尼教传至霞浦的西爽大师,应师承自高佛日,为呼禄法师的再传弟子,观其名号,亦应为胡人,再由他传至四都渔洋龙溪村人陈诚庵,由陈诚庵再传至孙绵,则传承关系为呼禄(胡天尊)→高佛日→西爽大师→陈诚庵→孙绵→林瞪。若以一辈相差20至25年计算,自843年摩尼教遭禁至966年孙绵建寺,共历123年,传5代,时间上大致吻合。
关于林瞪之生平,与《富春孙氏族谱》比,林氏族谱的记载则更为周详。如清同治十一年抄本《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载:
瞪公,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1003年)二月十三日生,行二十五,字□,娶陈氏,生二女……公年二十五,乃弃俗入明教门,斋戒严肃,历二十有二年,功行乃成。至嘉祐四年(1059年)己亥三月三日密时冥化,享年五十有六,葬于所居东头芹前坑。
公殁后灵感卫民,故老相传,公于昔朝曾在福州救火有功,寻蒙有司奏封“兴福大王”,乃立闽县右边之庙以祀之,续蒙嗣汉天师亲书“洞天福地”四字金额一面,仍为奏封“洞天都雷使”,加封“贞明内院立正真君”,血食于乡,祈祷响应。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林瞪为柏洋乡上万村桃源境人,[11] 诞生于北宋真宗咸平癸卯(1003年)二月十三日,于天圣五年(1027年)25岁时“弃俗入明教门”,拜孙绵为师,后成为“传教宗师”(霞浦科仪书《送佛文》)。卒于嘉祐己亥(1059年)三月初三日密时,享年五十七岁,死后葬于上万村芹前坑,至今墓址尚存。“娶陈氏,生二女”。林瞪生前所育二女见载于上引《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文曰:
瞪公……长女屏俗出家为尼,卒附父墓左。次女适□,卒祔父墓左……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可见,林瞪之长女终身未嫁,随母陈氏在龙首寺出家。次女曾出嫁,后皈依龙首寺。二女卒后皆葬于林瞪墓之侧。村民至今仍称此二女为龙凤姑婆,《乐山堂神记》第37行所见“芹前坑龙凤姑婆”即此姊妹二人之谓也。

上万村芹前坑西侧姑婆宫遗址
根据林氏宗谱,林瞪排行二十五,故而有“林廿伍公”之称。《兴福祖庆诞科》记述说:“恭维兴福都雷使林公二十五真君,生于济南八世,聪明正直,为神承基藏教,踪迹存于乐山,司土安民,恩被沾于福地。”但有的文献称之为“林伍公”或“林五公”,恐有误,抑或漏写“廿”字所致。在孙绵大师去世后,林瞪传承其衣钵,继续弘扬明教,使明教在这一时期得以发扬光大。他去世后,传其位于陈平山尊者。林瞪以其丰功伟绩与巨大影响力而被当地公认为摩尼教教主。值得注意的是,在霞浦科仪书《乐山堂神记》第15~18行却出现有这样的记载:
灵源传教历代宗祖:胡天尊祖师、胡古月祖师、高佛日祖师。乐山堂开山地主孙绵大师、玉林尊者、陈平山尊者……
孙绵与陈平山之间原本属于林瞪的位置却被“玉林尊者”所取代了。至于“玉林尊者”一名,除该文献外再未出现过。笔者经考证认为,所谓“玉林尊者”乃信徒对林瞪的尊称也。[12]
二、林瞪与摩尼师祈雨
摩尼师以善于祈雨而闻名。如《唐会要》曰:“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13] 而《旧唐书》又有记载说:“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14] 对于二载之别,岑仲勉氏已有考证:
余按《元龟》一四四云:“以久旱令阴阳人术士陈混常、吕广顺及摩尼师法术祈雨。”则阴阳人与摩尼师显分两途,《旧书》、《会要》各取一节耳。[15]
此结论可信,说明阴阳人虽与摩尼师一样具有祈雨之能,但二者应有所区别。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一度禁断摩尼教:“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16] 从开元“禁断”到贞元间令摩尼师祈雨,说明唐政府对摩尼教的态度有所变化,不仅认可了摩尼教,而且对它的态度也开始由排斥向信服转化。
景德元年(1004年)高昌回鹘入宋朝贡。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秋七月己丑条载:
上谓侍臣曰:“近颇亢旱,有西州入贡胡僧,自言善咒龙祈雨。朕令精舍中试其术,果有符应。事虽不经,然为民救旱,亦无所避也。”
这里出现的“胡僧”究竟是指佛僧还是摩尼僧,无法确定。观其“善咒龙祈雨”之文,笔者认为当与摩尼教有关,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开元七年(719年)如长安的吐火罗国大慕阇,此人即善“解天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17]然无证据推定与摩尼教之关系,故只能书此存疑。
这些记载尽管很珍贵,但毕竟一鳞半爪,难窥全豹。幸运的是,在霞浦摩尼教文献中却保留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陈宝华法师传用的《祷雨疏奏申牒状式》,计有71页,内含《牒皮圣眼》、《牒皮式》、《奏申额式》、《取龙佛安座牒式》、《安座请雨疏式》、《牒雷公电母》、《牒本坛》、《申东岳》、《请龙佛祈雨谢恩词意式》、《祈雨谢恩牒式》、《谢雨完满疏》、《谢雨申唤应》、《谢雨献状》、《奏三清》等多篇文字,反映的是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内容繁杂而有趣,如《牒皮圣眼》(图1)有文曰:
福宁州福安县城隍大王、本坛灵相、度师、诸大官将吏兵,钟龙圣井,感应行雨……瑞山堂护佛伽蓝真宰、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拏云使者、雨部一切神众、五谷大道真仙、田园公母禾稼神君、临水崇福太后元君、沿途诸宫大小明王、当境土主、里域正神、境内诸宫大小明王,凡祈雨司额写:大云祈雨坛;谢恩即写:电光植福坛。
其中的“灵相”一词,又见于敦煌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编号S. 3969+P.3884):“形相仪第二。摩尼光佛顶圆十二光王胜相,体备大明,无量秘义……诸有灵相,百千胜妙,寔难备陈。”[18] 可见,唐代“灵相”本义在于表示神祇的美妙形象,但南宋时代的一件道教文献却以“灵相”表示摩尼教之神祇:“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19] 福建晋江草庵所在地苏内村有一供奉摩尼教神明的境主宫,“寝殿粉壁上画‘五境主’——居中摩尼光佛,左一‘都天灵相’(又称灵圣公);左二曰境主公;右一曰‘秦皎明使’(又作千春公);右二曰‘十八真人’……村人以摩尼佛、都天灵相、秦皎明使为五境的主神”。[20] 不管是“灵相土地”还是“都天灵相”,都应该是从唐代摩尼教写本中的“灵相”直接衍化过来的。[21] 但在福建地区,“灵相”一词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林瞪其人,与唐代写本所见“灵相”并非一码事。霞浦本《乐山堂神记》第11~13行有“本坛明门都统威显灵相、感应兴福雷使真君、济南法主四九真人”之谓,《明门初传请本师》凡二见,分别写作“本坛祖师、明门统御威显灵相、洞天兴福雷使真君、济南四九真人”(第25~26行)和“都统威显灵相、度师、四九真人”(第19行);陈培生法师传用《摩尼施食秘法》载为:“本师教主、灵相、度师、四九真人。”该等名目均为林瞪的不同尊号或封号。推而论之,《牒皮圣眼》中的“本坛灵相、度师”也应指代林瞪无疑。
《牒皮圣眼》开首所祈求的神灵为“福宁州福安县城隍大王”,此名在《牒皮式》中也有出现:“摩尼正教主行祈雨济禾,保苗祈熟去事渝沙睍达臣厶谨封。背面写:大云祈雨坛;右牒请福宁州福安县城隍大王。”如所周知,福安县初建于南宋淳佑五年(1245年),直隶福建路福州。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福安县改隶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福宁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福安县隶属福州府。成化九年(1473年),福安县属福宁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宁府,福安县隶属福宁府。可见,该文献抄写的时代有二种可能:或在1286年至1369年之间,或在1473年至1734年之间。

图1 《祷雨疏•牒皮圣眼》
写于《牒皮圣眼》之前同属《祷雨疏》的失名文献后半部(前部残毁)中二度出现有“玄天上帝真武菩萨”,显然为《乐山堂神记》第4行之“北方镇天真武菩萨”之异写,指镇守北方的道教大仙——真武祖师。真武者,原名玄武,“祥符间(1008~1016年),避圣祖(即赵玄朗)讳,始改玄武为真武”。[22] 元朝大德七年(1303年)加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朱棣1402年称帝后,再加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民间习称之为菩萨。“玄天上帝真武菩萨”之称当来自于朱棣给真武所加封号之民间化写法,当晚于1369年,故可推定《祷雨疏》抄写于1473年至1734年之间,而其范本格式的形成则应比较早,当出自林瞪之手,以后代代相传,沿用至今。科仪书是法师做法时的工具书,法师写牒文,具体地点是根据实施法术的地点和求法者不同和而临时现填写上去的(原来该位置上是空格),而施法内容和程序则是固定不变的。法师传法给弟子时都是让弟子抄一本该法书,所以,上述断代只能是该科仪书抄写的时代。福安县位处霞浦县西邻,说明当时林瞪的影响曾扩延至福安县一带。
近期,在霞浦上万村新获《北宋前津门救火林瞪公求雨秘决》抄本一册,计有26页,记载了林瞪祈雨的仪式与咒语等,明显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容另作探讨。
苍南《林氏宗谱》(清嘉庆二十三年抄本)收录有林登翰所撰《八世祖瞪公石塔记》,文曰:
上万之西行里许名曰大坂洋,其先有喜雨亭,祀瞪公像,凡值岁大旱,祈雨五境迎会,必于此驻跸。越嘉庆丙寅岁九月,喜雨亭坏,经今十余年,并无一咏及者,翰因与鼇慨然曰:“前人遗迹,不可沦亡,但木易朽而石则亘古常新,请以旧址创石塔可乎?”佥曰:“善!”遂鸠赀倩石工镌公遗像及温康诸神于左右,阅日月落成,由是五境之祈祷者咸称为便,今届修谱,所有词宇传赞更详,莫不照耀简端,而谓一塔之微,毋庸秉笔乎?不揣谫陋,特志之,以垂不朽云。
裔孙庠生登翰百拜谨撰。
这些记载都说明,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以善于祈雨,造福乡邻,从而赢得了世人的尊崇。直到今天,村中的老人还常讲,每逢大旱时节,村民们只要摆好祭坛向“林公”求雨,一天之内必定会有甘霖降下。
三、摩尼教绢画所见的林瞪
近期,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收藏的一幅元末着色绢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该画面积142cm×59.2cm,1966年入藏该馆,此前的传承了无记录,关于其来源,1988年发表的《大和文华馆目录》有极简单的说明:“从画风看,是元代后期宁波附近的专业画工制作。”很长时间,该画被误称作佛教《六道图》或景教绘画,近经日本学者吉田丰和美国学者古乐慈研究辨识,确认为摩尼教绘画。[23]古乐慈通过对画面的分析,认为其内容可分为五个层次。最上层表现天界,正中为一宫殿,内容为光明处女及其扈从访问天界;第二层居中有摩尼教神像(很可能是摩尼本人),右边有两个穿着白服的摩尼教选民(僧侣),一个坐着,可能正在说法,另一个站着,当为助手。左边穿红衣坐着的当为听法者,站其侧着黑衣者当为其侍者;[24] 第三层分成四个小格,分别代表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第四层描绘的是摩尼教概念中的阴司审判;第五层,即最下层描绘的为地狱景象。[25](图2)这一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图2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元末着色绢画
上述解释言之有据,揭橥了该绘画的摩尼教属性,功不可没。惟对第二层内容的解释有未备及可商榷之处,兹据敦煌文献略予辨证。
敦煌本《摩尼光佛法仪略·五级仪第四》(S. 3969)载:
第一,十二慕阇(中古波斯语možak,拉丁语magister),译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七十二萨波塞(中古波斯语ispasag,拉丁语episcopus),译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诞”(中古波斯语aftādān);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中古波斯语mahistag,拉丁语presbyter),译云“法堂主”(中古波斯语mānsārār,帕提亚语mānsarār);
第四,阿罗缓(中古波斯语ardawan,拉丁语electi),译云“一切纯善人”;
第五,耨沙喭(帕提亚语mi$ōšagān,拉丁语auditores),译云“一切净信听者”。[26]
在摩尼教等级排列中,作为第一品级的慕阇人数为十二名,拂多诞为七十二名,再下的默奚悉德为三百六十。这些应为中上层人物,再下为阿罗缓,为低级僧侣。以上四者皆为选民,被称为“义者”,属于僧侣。按照要求,一律穿白袍、戴白帽,即“素冠服”之谓也。耨沙喭,意为“听者”,与“义者”相对应,是摩尼教组织中最低一级,相当于佛教的居士,身着俗人装束,即“听仍旧服”者。大致相当于佛教的居士。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四日,某臣僚上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27] 这里的“侍者、听者、姑婆、斋姊”分别指男选民、男听者、女选民和女听者,[28] 相当于佛教的比丘、优婆塞、比丘尼和优婆夷。看来,如同佛教把信徒分为和尚和居士一样,摩尼教也把信徒分为选民(electi)与听者(auditors)二部。[29] 所以,将身着白衣和红衣者分别推定为“义者”和“听者”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但具体到这一幅画面言,做如此解释却颇有不通之嫌。首先,摩尼光佛端坐画面正中,如果是说法图,说者应该是摩尼光佛,而不应该是其座位前的“义者”;其次,如果是“义者”在说法,那么“听者”就应该跪坐其下,至少不会出现像本画面这样的平起平坐的场景;其三,如果称“义者”在说法,听众却只有一人也似有不合情理之处,与吐鲁番所见摩尼说法图迥然有别,后者一般都会有众多听法者,和佛教绘画所见说法场面颇类。
观绢画之工艺特点与艺术风格,言称出自宁波,不无道理。但虑及摩尼教一直不曾在宁波流行,故笔者怀疑该摩尼教绢画或应为霞浦之物。当笔者带着这些疑问询及霞浦上万村村民时,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绢画很可能为上万村祖传圣物之一,惜抗战时期失传。画面第二层居中的大像为摩尼本人,二侧所坐,右边身着白服者为明教教主身份的林瞪,左侧着红衣的为宰相身份的林瞪。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显然比古乐慈的解释要可取得多,更符合霞浦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旨趣。
上万村村民相传,林瞪曾在北宋时期出任过宰相之职,在闾山学法归来后法力高强,能除妖降魔,平生乐善好施,护国救民,御灾捍患,为普罗大众所景仰。嘉祐年间(1056~1063年)福州失火,林瞪因救火有功而被封为“洞天都雷使”和“兴福真人”。万历《福宁州志》记其事曰;
林瞪,上万人。嘉祐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遥告众曰:“我长溪上万林瞪也。”闽人访至其墓拜谒,事闻,敕封“兴福真人”。正德初,闽县令刘槐失辟,因祷之,夜梦神衣象服,告以亡处,明日果获。[30]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乾隆《福宁州志》卷32《人物志·方外》、民国《福建通志·列仙传》和民国《霞浦县志》卷38《列传》。从中可以看出,林瞪先“衣素衣”救火,又“衣象服”助人。
按,“衣素衣”同摩尼教“并素冠服”的习俗是相关联的,而所衣“象服”,为一种有彩绘的礼服,为王后及诸侯夫人所穿。《说文》:“襐,饰也。象服犹饰,服之以画绘为饰者”;唐代钱起《贞懿皇后挽词》:“有恩加象服,无日祀高禖。”身着象服表示高贵之意。此虽属传闻,可能反衬出林瞪身份较为高贵的史实。[31] 梦境中林瞪衣妇人所穿象服,此非常态,无疑在于彰显神秘色彩。以“衣素衣”与“衣象服”来解释绢画第二层内容,新鲜又可信。

绢画第二层内容
上文所言,林瞪继承摩尼教传统,以善于祈雨著称,当福州城门失火时,林瞪曾“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依常理,灭火应靠降雨而非靠扇,火借风势会愈加猛烈。故而笔者认为,林瞪之救火靠的仍然是雨,铁扇只不过是祈雨的道具。由扇致风雷,由风雷而致雨,终灭城门之火,故而林瞪才被封为“洞天都雷使”,既为“雷使”,则必与降雨有关。如此释之,得无可乎?上万村民间传说云:宋真宗时,福州知府将林瞪公救饥善举及法术高强等事上奏,真宗遂召林瞪公入朝并赐御宴。适逢福州鼓楼失火,林瞪遂顺手借三杯御酒向福州洒去,化作三阵红雨,熄灭了福州鼓楼大火。这个传说故事,更有助于解释绢画第二层画面的着装问题。
以“衣素衣”与“衣象服”来解释绢画第二层内容,言之成理,可以取信。[32] 但若以之与晋江市苏内村境主宫所见神明配置绘画相较,笔者觉得将其解释作摩尼光佛、秦皎明使和都天灵相等亦无不可,即居中者为摩尼光佛,左为秦皎明使,右为都天灵相。如前文所言,“灵相”乃福建摩尼教徒对林瞪的尊称,苏内村境主宫称之为“都天灵相”,意在表示林瞪具有经天纬地之神通。宋代白玉蟾在与彭耜的对话中谈及明教,言:“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33] 显然,这里的“灵相土地”与境主宫之“都天灵相”是相通的,皆为林瞪之称谓。林悟殊先生猜测“秦皎明使和都天灵相,可能就是由先意和夷数衍化演变出来的”。[34] 似有未妥。
复观苏内村都天灵相之木雕像,造型酷似霞浦柏洋乡迪惠宫之林瞪像,与柏洋乡龙首宫、林氏祠堂与福州明教文佛祖殿所见的林瞪也相差无几。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上述元末着色绢画也可以解释为中摩尼,左着红衣者为都天灵相林瞪,右着白衣者为秦皎明使。是以,可以认为,摩尼教由晋江灵源山北传至霞浦后,经过霞浦林瞪的改造,又由霞浦回传至泉州晋江一带,影响及于当今。
四、林瞪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摩尼教自唐代入华,命运多乖,惟因回鹘自763年始奉之为国教,才实现了柳暗花明大转折,4个世纪间,对回鹘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直到12世纪后半叶销声匿迹。[35]此后,摩尼教于世界范围内归于沉寂。然而,在中国东南一隅的福建,摩尼教却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得以幸存,生生不息,代传至今。霞浦、福州等地新近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文物,为我们揭橥这一现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可以看到,福建摩尼教与原始摩尼教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无不体现出林瞪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霞浦摩尼教顺利实现了由官方宗教向民间宗教的转型。摩尼教本是一个尊崇王权的宗教,宣称:“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36]把国王比作摩尼教信徒所崇奉的“朗日”与“满月”,强调王权,以迎奉统治阶级的思想。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教文献即带有明显的官方特点,如《摩尼教残经》可能为摩尼所撰七种著述之一《证明过去教经》之汉译本;[37]《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乃唐玄宗时在华摩尼传教师奉诏撰写的一个解释性文件。[38] 但自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禁绝摩尼教传播后,潜入福建的教徒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今存的霞浦文献,差不多都是科仪方面的内容,除了《摩尼光佛》对王权思想有所反映外,其余文献不复重见王权崇拜的内容,林瞪成为信徒崇拜的首要对象。早期入华摩尼教主要依托佛教,敦煌写本与汉文史籍多有反映。而霞浦则不同,佛教影响力锐减,逐步让位于道教与福建地方信仰,[39]这在《乐山堂神记》、《兴福祖庆诞科》、《点灯七层科册》、《明门初传请本师》及《祷雨疏》等众多文献中都有突出反映,只有《摩尼光佛》有所例外,主要依托的仍是佛教,而且从体例到内容,《摩尼光佛》都与霞浦其他科仪书迥然有别,说明《摩尼光佛》应为霞浦较早期的文献,受唐代摩尼教文献的影响较大。摩尼教在霞浦一带适应民情,脱夷化与民间化倾向渐趋明显,逐步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秘密民间法门——“明教门”。作为教主的林瞪,势必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其次,霞浦摩尼教的组织性得到空前加强。龙首寺建成于966年,至第二代寺主林瞪时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祖师制度,寺主嫡嫡相传,这在波斯、中亚等地的摩尼教中均无先例,在回鹘及唐代中原地区也未有所闻,惟霞浦有之,当系受中国佛教教派(地论派、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祖师传承制度的影响所致。这一制度后来又由霞浦而北渐浙江,仅在温州就形成斋堂40余处,而温州之摩尼教又来自霞浦一带,苍南《林氏族谱》奉林瞪为八世祖。故而可推定,温州明教斋堂的形成,当是受龙首寺的影响所致。[40]
其三,林瞪与摩尼教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宋代以来,霞浦摩尼教势力逐步壮大,先是向北传至浙江温州,向西延及西邻福安,向南则扩及省垣福州。前三者已有述及,不赘,这里仅就福州之福寿宫略作考述。前引林瞪裔孙林登鼇撰《八世祖瞪公赞》记载:
公于宋嘉祐间福州回禄救援有功,封为“兴福真人”,建庙于省垣,庙食百世,其子若孙亦各立庙宇,以每年二月虔备祭品,庆祝华诞,岁时伏腊皆有祭,凡有求必祷(灵)[41],有祷必应焉。嗟呼!公以一布衣而享祀不忒,流芳百世,揆之古人,若关公尽忠事汉,死为帝君;岳将竭力佐宋,没为正神。虽显晦不同而乃圣乃神,宁不与之后先济美哉!
这里明言林瞪因在福州救火有功而被封为“兴福真人”,而且“建庙于省垣,庙食百世”,这应是官方的举措。寺址所在,前引《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载曰:“故老相传,公于昔朝曾在福州救火有功,寻蒙有司奏封‘兴福大王’,乃立闽县右边之庙以祀之。”
福寿宫位处乌山角下南门外十八洋路之浦西洋,为闽县之右(南面),地理位置完全吻合。故“闽县右边之庙”指的就是今浦西之“明教文佛祖殿”。由于摩尼教不再流行,对今人来说,“明教文佛祖殿”的宗教属性不够明确,为申请合法宗教身份,于1998年改名为“福寿宫”,胪列道教庙宇,但村民耆老皆言祖辈供奉该寺神明的仪式很独特,与道教、佛教都大不相同。
近年,李林洲通过田野调查,认定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为摩尼教遗址:“清乾隆年间铸铁元宝炉。上有浮雕铭文‘度师真人,明教文佛,清乾隆庚戌年花月,本里弟子萧兆鹏喜舍’。明教即摩尼教,文佛即摩尼佛。”[42] 文中将福寿宫定性为摩尼教寺院,颇得鹄的,唯把文佛看成摩尼佛之同义语显然有些欠妥。林悟殊指其谬,称“‘文佛’未必就是摩尼佛”。[43] 霞浦本《摩尼光佛》中将释迦文佛和摩尼光佛并列,足证文佛和摩尼光佛非一,但林先生完全否认福寿宫之摩尼教属性,则似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一者,林先生考证“明教文佛”与摩尼教无关,而霞浦本《摩尼光佛》却将释迦文佛与那罗延佛、苏路支佛、摩尼光佛及夷数和佛并列,合为摩尼教信仰的五佛。[44]其中的摩尼光佛,在吐鲁番出土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残片M 801中被称作弥勒佛,并称是由他打开了乐园的大门。[45] 霞浦文献中也多次提到弥勒,[46]体现了弥勒信仰在摩尼教中的盛行。释迦文佛即明教文佛,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民间宗教不若正统宗教那么严格,完全可以理解。二者,林先生断言:“在华摩尼教僧侣有法师之称,但无‘度师’之谓,吾人不可勉强把‘度师真人’推测为摩尼师。”[47] 还有学者认为:“这(指福寿宫——引者)是一座道教色彩很浓的明教寺院,度师真人系何方神圣有待考明,大概是名摩尼师,摩尼教对高僧法师都称师,定光古佛就被称为师。‘真人’是寺院道教化后不明真相的信徒胡乱加上去的,本始的称呼应是‘度师’。”[48] 其实,“度师真人”来源有自,并非“胡乱加上去的”。在前举霞浦本摩尼教祈雨文献《祷雨疏》、《求雨秘诀》和《明门初传请本师》中即多次出现“度师”一词,而且在《祷雨疏·牒本坛》中还有“天门威显灵相、洞天兴福度师、济南法主四九真人”之谓,用以指代林瞪,福州福寿宫供奉的对象其实就是摩尼教教主林瞪。三者,林先生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元宝炉铭文的落款,认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不仅福州,东南沿海的其他地区,早已没有摩尼教流行了”[49]。然而,霞浦文献却证明,摩尼教在霞浦西北部一带一直流行至今,而且在1473年至1734年之间曾流传至福宁州福安县一带。当然,这些并非林先生的疏失,乃因《摩尼光佛》、《祷雨疏》等文献均发现不久,迄今尚未刊布所致也。前引《八世祖瞪公赞》所言清代福州之林瞪庙,当即福寿宫之前身,以“度师真人”林瞪和明教文佛为主供,只是被披上了道教的外衣而已。[50]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福寿宫大殿之古联“朝奉日乾坤正气,夕拜月天地光华”[51] 也是颇符合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之习俗的。[52]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闽侯县上街镇石砂村有一民间信仰宫庙,同样供奉度师真人和明教文佛,当地信徒明确告知,该庙为其祖先约200年前在福州经商时作为浦西明教文佛祖殿信徒而从祖殿分炉来的。[53] 综合上述因素,可以认为,言称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为摩尼教寺院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证据丰富且确凿的。主祭林瞪,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仍可称之为林瞪庙。福寿宫当为霞浦龙首寺(乐山堂)、宁波崇寿宫、泉州刀石山摩尼寺、晋江华表山草庵、温州平阳潜光院之外的第六所摩尼教寺院,幸存至今,是世上仅存的唯一的摩尼教寺院,堪称古代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值得保护与研究。

福州福寿宫明教文佛和度师真人造像
对于霞浦摩尼教的发展,林瞪之功居其首,尤其是在瞪曾充任龙首寺第二代寺主期间,霞浦摩尼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流风所及,闽浙摩尼教渐次得到发展,并最终于闽浙一带形成了一个颇具地方特色民间秘密法脉——“明教门”。职是之故,林瞪便被霞浦乃至福安、温州、福州、泉州等地的摩尼教徒尊奉为共同的教主了,其身份也被逐步神圣化。在霞浦本摩尼教文献中,林瞪被称作“本坛明门统御威显灵相、洞天兴福雷使真君、济南四九真人”(《乐山堂神记》第11~13行),“职标雷部,掌威权法,阐明门,兴正教,敕封感应兴雷真君”(清抄本《兴福祖庆诞科》,第94~95行)。据当地民间传说,这些都是宋政府赐予林瞪的封号。苍南《林氏宗谱》(清嘉庆二十三年抄本)收录的林瞪裔孙林登鼇于嘉庆二十二年(1871)所撰《八世祖瞪公赞》更是称颂有加:“如我祖讳瞪公尤罕匹焉。族人以公护国救民,御灾捍患,久已脍炙人口,特有(未)[54] 有赞焉以纪之。鼇敬仰公之为人,正气塞乎两间,不屑屑于富贵,不戚戚于名利,因非凡人所可及矣。”对林瞪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从中不难看出,当地民众对林瞪的崇拜非同一般。
每年从农历二月十二日开始一直到二月二十一日,在柏洋乡之柏洋村、上万村和塔后村都有祭祀林瞪的活动,活动主要内容有文艺演出、迎神活动、祈福祭祀、拜谱仪式、文物移交等,其热闹程度甚于过年。[55] 直到今天,霞浦上万村仍保存有五件据称林瞪生前所使用过的法器,其中有刻着“圣明净宝”和“五雷号令”的印章两枚,还有民间俗称作“蛤蟆炉”的青铜角端,甚至还保存有林瞪妻陈夫人生前所用的耳环等金、银饰品等。通过有关专家鉴定,上万村的青铜角端与故宫太和殿的一对角端极其相似,当系明代或明以前的遗物,而“圣明净宝”印章,显然是明教教主专用的权威凭信,“五雷号令”印章当为林瞪专用于祈雨之物,自无疑问。上述这些实物足证林瞪在“明教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霞浦上万村藏“圣明净宝”与“五雷号令”印章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摩尼教研究”(编号07BZS003)阶段性成果。本文的撰写得到北宋摩尼教教主林瞪公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及其助手张凤女士的大力协助,同时也得到福州市台江区浦西村福寿宫管委会主任肖家铨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于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1]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总97辑),第136页。
[2] 禅洋村迄今尚存有孙绵大师墓遗址。
[3] E. Schafer, The Empire of Ming, Tokio 1954, pp. 102, 106;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4] 王媛媛《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杨富学《回鹘摩尼寺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异化》,《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2期。
[5] [明]永觉元贤《永觉和尚广录》卷24《春日同诸子游云际山》,《续藏经》卷72,No.1437,页523a。
[6]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
[7] 陈进国、吴春明《论摩尼教的脱夷化和地方化——以福建霞浦县的明教史迹及现存科仪本为例》,提交“民间儒教与救世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佛光大学,2009年6月9-11日)。
[8]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总97辑),第156页。
[9] [明]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0]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99《福建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516页。
[11] 据林氏族谱记载,林瞪系唐代著名孝子林攒的裔孙。
[12]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总97辑),第138页。
[13] [宋]王溥《唐会要》卷49《摩尼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12页。
[14]《旧唐书》卷13《德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0页。
[15] 岑仲勉《摩尼师与阴阳人》,《唐史余审》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131页。
[16] [唐]杜佑《通典》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页注文。[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同载,但称其为八月十五日,见《大正藏》卷54,No. 2126,页253b。
[17]《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6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19] [宋]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卷1,《道藏》第3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页114下~115上。参见饶宗颐《穆护歌考》,《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501~502页。
[20] 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21] 林悟殊《泉州晋江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6页。
[22]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9。
[23] Zauzsanna Gulacsi, A Visual Sermon on Mani’s Teaching of Salvation: AContextualized Reading of a Chinese Manichaean Silk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of the Yamato Bunkakan in Nara, Japan,《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XIII,2008年,pp. 1-16;吉田丰,“宁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图」の解釈をめぐつて”,《大和文华馆刊》第119号,2009年, 第3~15页。
[24] 日本学者泉武夫认为第二层表示的为儒士与道士朝拜摩尼的画面。见其所著“景教圣像の可能性——栖云寺藏传虚空藏画像について”,《国华》第1330号,2006年,第12~13页。
[25] Zauzsanna Gulacsi, A Visual Sermon on Mani’s Teaching of Salvation, pp.3-6;ZauzsannaGulacsi, A manichaean Portrait the Buddha Jesu (yishu fo zheng): Identifying aTwelf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eiun-ji Zen Temple, Artibus Asiae 69/1, 2009, pp. 102-104. [美]古乐慈著,王媛媛译《一幅宋代摩尼教〈夷数佛帧〉》,《艺术史研究》第10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8~150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225页。对音采自Samuel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China, Brill:Leiden-Boston-Köln, 1998, p. 84.
[27]《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八~七九。
[28] A. Forte, Deux études sur le manichéismechinois, T’oung Pao 59, 1973, pp. 234-235.
[29] Éd. Chavannes -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1 nov.-déc., p. 554; 马小鹤《粟特文’δw wkrw ’ncmn(二部教团)与汉文“四部之众”》,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13~433页。
[30] 万历《福宁州志》卷15《仙梵》(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31] 陈进国、林鋆《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32] 霞浦民间传林瞪曾为北宋宰相,会不会与林瞪“衣象服”被讹作“衣相服”(宰相之官服)有关?未可知也。
[33]《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道藏》第33册,第115页。
[34] 林悟殊《泉州晋江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8页。
[35]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8~197页;杨富学《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8~146页。
[36] 敦煌写本《摩尼教残经一》,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37] 林悟殊《〈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100页。
[38] 石田幹之助《敦煌发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に见えたる二三の言语に就いて》,《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岩波书店,1925年,第157~172页;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卷的缀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7~202页。
[39]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总97辑),第166~172页。
[40] 林顺道《摩尼教传入温州考》,《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1页;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总97辑),第158~166页。
[41] 此处之“祷”,意不通,据上万村藏清抄本《林氏族谱》,当改为“灵”。
[42] 李林洲《福州摩尼教重要遗址——福州台江义洲浦西福寿宫》,《福建宗教》2004年第1期,第44页。
[43] 林悟殊《福州浦西福寿宫“明教文佛”宗教属性辨析》,《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18页。
[44] 马小鹤《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复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0~114页;林悟殊《明教五佛崇拜补说》,《文史》2012年第3期(100辑),第385~408页。
[45] J. P. As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75, p. 62.
[46] 清抄本《兴福祖庆诞科》第46行、《奏申牒疏科册》第47行、《高广文》第37行,等。
[47] 林悟殊《福州浦西福寿宫“明教文佛”宗教属性辨析》,《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2页。
[48] 陈一舟、涂元济《福建摩尼教寺院遗址考》,《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2页。
[49] 林悟殊《福州浦西福寿宫“明教文佛”宗教属性辨析》,《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0页。
[50] 陈一舟、涂元济《福建摩尼教寺院遗址考》,《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0~82页。
[51] 李林洲《福州摩尼教重要遗址——福州台江义洲浦西福寿宫》,《福建宗教》2004年第1期,第44页。
[52] 马小鹤、芮传明《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研究》(上下),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5卷,1999年,第263~281页;第16卷,1999年,第326~342页。
[53] 李林洲《福州摩尼教重要遗址——福州台江义洲浦西福寿宫》,《福建宗教》2004年第1期,第44页。
[54] 此处之“有”,意不通,据上万村藏清抄本《林氏族谱》,当改为“未”。
[55] 林子周、陈剑秋《福建霞浦明教之林瞪的祭祀活动调查》,《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第82~85页。
【编按】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9~124页,附图有所增补,引用请参考原文。